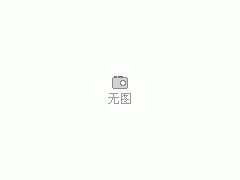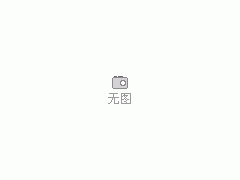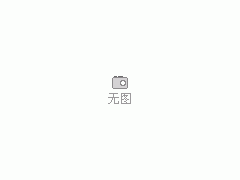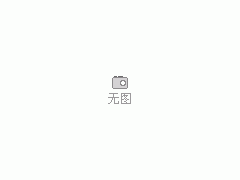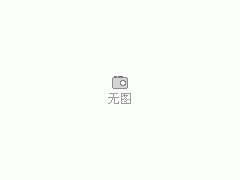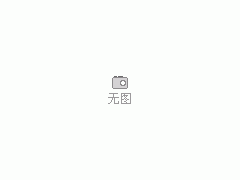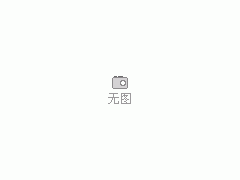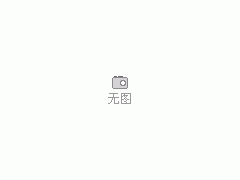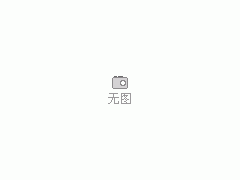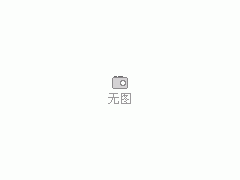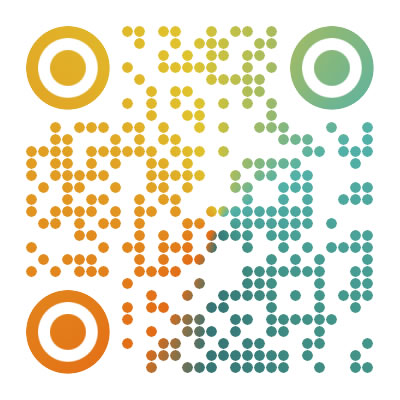友人發來一張老照片,標明”中共錦州市第三屆代表大會南票全體代表合影”,頓時勾起了兒時的記憶。

照片中好幾位都曾經是我們家的近鄰。
其中前排左數第二位,長得像彭真的那位,是馬大爺馬達(當時的局長),與我家住一棟房(當時叫4棟),中間隔著韓大爺家。馬大爺家是4棟6號。(后來改為41棟6號)
他右邊那位是段大爺段相慶(當時的黨委書記)住我家后棟房(3棟6號。后來我們住一棟房)。
段大爺右邊的是劉大爺劉忠厚(當時局組織部長)住我家后兩棟房(1棟1號)前些日子我寫回憶早逝的三哥“禿驢”就是他老人家的三兒子。他四兒子,我們是一起下河摸魚的好朋友 ,他家房后就是托兒所。
后排左數第一位是齊叔齊寶德(當時運輸處黨總支書記)住與我家隔路斜對房頭的12棟6號(后來的王國華家)。
后排左數第二位是李大爺李啟瑞(局工會主席)住在齊叔家隔一棟房房后(10棟6號)。
今天先說馬大爺。
我家是1959年10月末來南票的。那時拉貨的火車剛通,還不通“票車”(客車)。接我們的藍叔叔先安排我們在錦州辦事處住了一夜,第二天下午坐劉玉書叔叔(后來在醫院開車)開的大面包車(當時叫中卡,像醫院救護車似的但是綠色)來的。那時的住宅絕大多數還沒住人家,托兒所和“前十棟”即報社(最早叫大食堂那時還沒蓋以南的那一片)那兒挖的蓋房子的地溝還能看到棺材板子。
馬大爺家早就來了,他家與我家隔著韓大爺家(那時還沒搬來來,4棟1號李大爺家來了)。只聽人們喊他馬局長,鄰里們常來往,幾乎感覺不到尊卑貴賤。
馬大爺常穿個褐色的粗麻袋呢子半大衣,大嗓門說話聲音很高,很侉,山東不山東,河北不河北那個味兒,見面總好捏我鼻子......
那時礦務局就有一輛華沙轎車,還沒時興局長專車。開車的是住在前棟房的趙信叔叔和后棟房的王鳳起叔叔。那時礦務局機關在與黃甲屯車站(那時叫乘降所)東邊平行的那趟紅磚平房辦公,轎車就停在第三棟房中間。
有一回去沈陽開會,出了火車站,秘書去車站里邊打電話,聯系來車接他們,馬大爺一個人站那兒等著。可能是見他穿個粗麻袋呢子衣服“穿得土”,圍上來一伙人,問話一聽口音傝啦吧唧,不容分說,連推帶搡地就把他弄上大卡車,拉“盲流勸阻站”去了。
“盲流勸阻站”,就是臨時集中收留關里跑東北來找工作的流動人口的地方,有人組織他們學習,勸他們返回家鄉參家集體生產勞動,不要盲目流動。
那時我還不知道“盲流”是啥意思,反正感覺不好。
后來知青下鄉招工當了鐵路養路工,慢慢熟了,跟師傅們嘮嗑,才知道四工區我的那些師傅們,也都是當年的盲流,就連我們段黨支部書記,機關團委書記............都是盲流。
待到去車站里頭打電話,聯系好了車的秘書來接馬大爺時,卻怎么也找不到他了!好幾撥人,在沈陽火車站候車室,票房子,站前廣場吆喝“馬局長”,省里也急了,薛奇還等著聽他匯報呢,就掛電話到礦務局追問,開會的馬局長怎么還沒到?礦務局回答 早就坐火車去了......
馬大爺被關在盲流勸阻站干著急,要找他們領導理論,人家說你不夠格;要打電話聯系,人家不讓;沒人相信他是來開會的,都認為他是跑盲流的;他急得直跳腳兒,也沒法聯系人解救他.徹底感受到了沒法聯系的尷尬。
這是我上小學二年級時聽串門兒的馬大娘說的。
馬大娘總上我家串門,還沒進屋就喊“小孩兒娘”---她管我母親叫“小孩娘”。馬大娘不上班,她很巧,做的發糕可真好吃,是苞米面摻白面的那種,她做的條絨棉鞋也漂亮,還會拿皮子研鞋口,用布條盤衣服鈕扣瓣。
他家五口人,大兒子看樣子比我姐姐年齡還大,那時我姐姐讀中學,他就已經上班了。
聽說他有“神經官能癥”,醫生讓他住院療養。馬大爺說,不就是夜里睡不著覺嗎?干點兒力氣活兒就好了。就讓他上九龍山下河北岸的那個磚瓦廠跟工人一樣在土坑挖土,推轱轆碼子車運土,和泥 燒窯 出磚......。
他家就有一個女孩“大晨子姐姐”,高高的個兒,不胖不瘦,梳一條大辮子,文文靜靜的,常帶我們玩兒。有一回我們一起去王八溝採槐樹花,回來包菜餑餑吃(那時糧食不夠吃)吃得我們臉都浮腫了,母親說中毒了。后來回憶是我們不認識,把粉紅色的槐樹花也混著采摘回來吃了。
三年級時過春節,大年初一天還沒大亮,我還沒起來,大臣子姐姐就來拜年了。
我不好意思爬起來,就瞇著眼睛假裝睡覺,大臣子姐姐和父母說著話,卻把手伸我被窩里,來回揉搓,說大年初一睡懶覺,一年都是懶蛋! 我才假裝坐起來,揉眼睛穿衣服......
他家援朝哥最小,比我大兩歲,他自豪地說是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那年生的,他不太愛說話,也不像我們那么野,但他的小人書我隨便拿,有時也跟我們玩兒。我姐姐放假回家時,他們都問過我姐姐題......不久我家搬到了前一棟房1號(即42棟1號)與齊寶德叔叔家對房頭,他家也搬走了。
 鍋爐之家客服熱線:
鍋爐之家客服熱線: